|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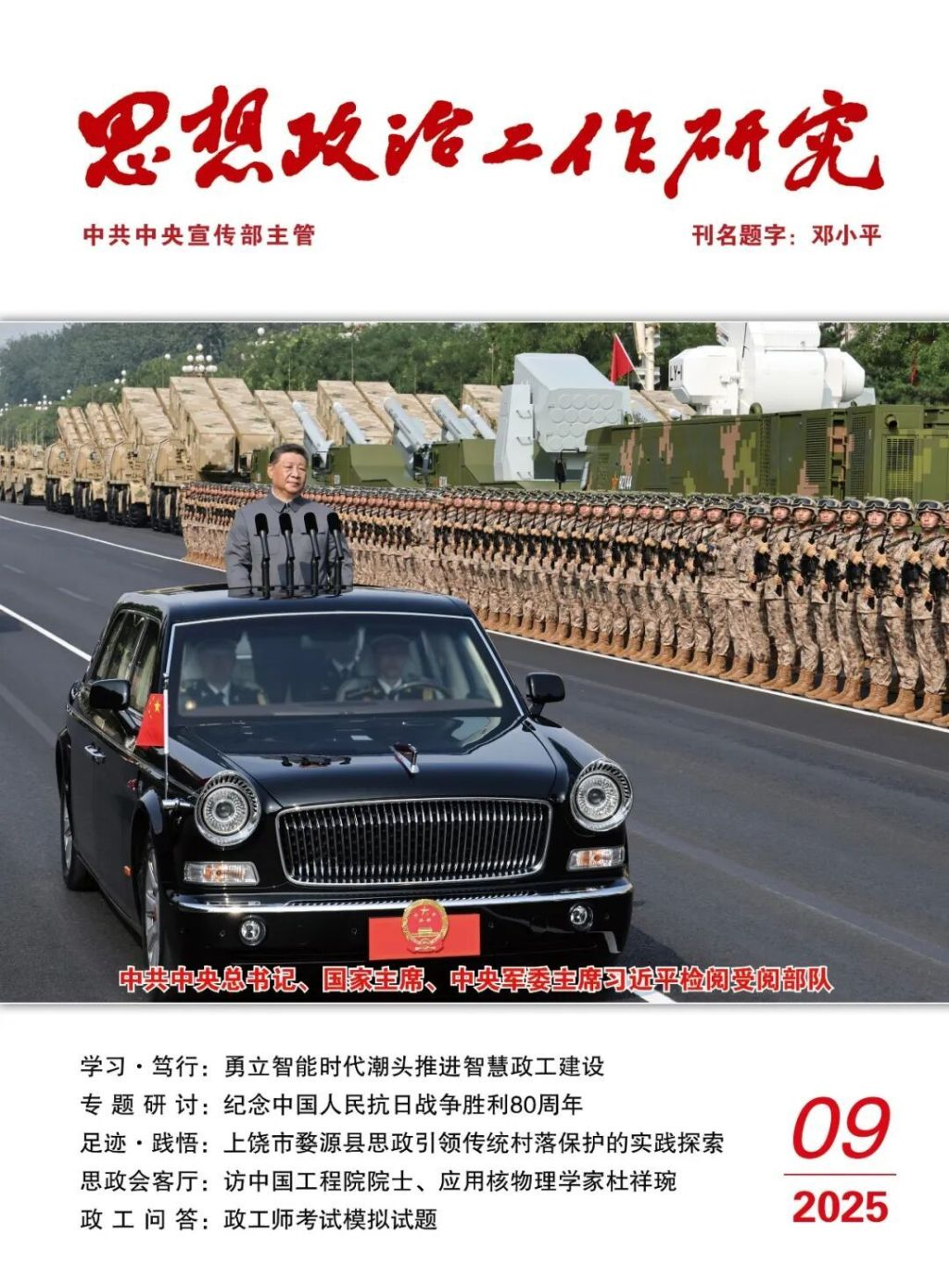
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思想(以下简称“‘三结合’思想”),是指将正规军、地方武装与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强调各种力量密切配合、适时转换,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这一思想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理解毛泽东“三结合”思想在抗日战争中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深刻感悟其在各领域的影响和对新时代新征程的重要启示。
毛泽东“三结合”思想在抗日战争中的发展
“三结合”思想的早期萌芽。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吹响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在党的号召指引下,东北军、部分警察部队及群众组成义勇军、救国军等地方武装,组建抗日游击队,以游击战争打击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并逐步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为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贡献力量。局部抗战期间,党直接领导和间接支援的各类抗日武装,通过多元协作抗击日伪军,探索出武装力量配合的有效模式,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为毛泽东“三结合”思想的形成奠定重要基础。
“三结合”思想的初步探索。全面抗战开始至1940年底,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同时借鉴土地革命经验,建设根据地和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及群众武装,三种力量协同配合,初步探索出适合抗战的武装力量体制。改编后的八路军、新四军成为敌后主力军,不断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并壮大部队;根据地地方武装由八路军抽调干部组建游击队,联合地方政权组成游击总队等,成为游击战争重要力量;民兵、自卫队作为群众武装,承担侦察、运输等任务,是地方武装和主力军的后备力量,成为敌后抗战的生力军。
“三结合”思想的正式形成。1941—1943年春夏,敌后根据地面临日军“大扫荡”、国民党不断掀起的反动高潮与华北自然灾害等困难,为持续抗日,党中央和毛泽东认识到均衡发展主力军、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的重要性。各根据地开展“精兵简政”,缩编机关、整编部队,提升八路军、新四军战斗力并减轻人民负担。在地方武装建设上,基于主力部队地方化组建军区、军分区,健全领导制度;在群众武装建设方面,通过颁布条例提供制度保障,建立人民武装委员会加强组织领导,开展宣传动员与教育训练,使三种武装力量协同作战,激发群众抗战热情,“三结合”思想基本形成。
“三结合”思想的发展完善。1943年夏秋,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预见抗战后期将转向正规战争,需实现从游击战争到正规战争的转变,为武装力量发展指明了方向。1944年9月,中央军委高干会议提出作战形式从游击战为主转向运动战、阵地战为主,大量发展主力军、编组正规兵团的方针。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肯定了“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作用,对加强各武装建设提出了要求,各根据地据此恢复扩大主力军并整训,“三结合”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日本投降后,为歼灭拒降日军和应对内战,各战略区组建野战兵团,根据地重组军区机构、升级地方武装、动员民兵及群众参军,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毛泽东“三结合”思想在抗日战争中的影响
毛泽东“三结合”思想作为注重发挥人民群众整体威力的人民战争思想,在抗日战争中释放了强大能量,具有重要国内国际影响。
“三结合”思想的实践探索了受压迫民族实现民族解放的中国共产党模式。“三结合”思想打破了传统的战争观念,强调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展示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让全世界人民尤其是受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认识了一种全新的战争模式,即通过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形成全民参与的战争态势,从而弥补武器装备和军事力量的不足。民兵和自卫队虽然装备简陋,但他们凭借对家乡的热爱、熟悉和坚定的抗战意志,积极参与战斗,对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这种人民战争的实践,为世界弱小国家开展民族解放战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结合”思想的实践为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有效的组织保证。“三结合”思想强调抗日作战中主力兵团与地方武装、群众武装密切配合,战略上形成梯次配置,并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转换。主力兵团是敌后抗战的骨干力量。在作战中,主力兵团主要是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攻坚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各方向战略展开后,主力兵团先是创建抗日根据地作为敌后抗战的重要依托,再组织发展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地方武装主要是在各自的根据地内,在民兵、自卫队的配合下开展灵活多样的游击战,牵制敌人、消耗敌人,为主力兵团创造有利的作战条件。非作战时,地方武装则加强根据地建设,协助地方政府开展群众工作,扩大自身力量。群众武装则不仅是主力兵团和地方武装的后备力量,而且还是敌后支前的主要力量。他们凭借对地形与民情的熟悉,以地雷战、麻雀战等灵活战术袭扰日军据点、破坏交通线,承担侦察、警戒、传递情报等任务;同时,还积极参与后勤保障,通过筹粮、做军鞋、运送伤员等行动支援正规军作战,构建起全民抗战的网络体系,使日军陷入“处处受敌、寸步难行”的困境,成为持久抗战的坚实后盾和重要法宝。
“三结合”思想的实践彰显了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三结合”思想强调战争力量的系统性集成。在战略层面,主力兵团作为核心骨干,承担战役级攻坚任务;在战役层面,地方武装作为桥梁纽带,发挥区域性作战功能;在战术层面,游击队与民兵作为“末梢力量”展开麻雀战、破袭战等。这种“战略—战役—战术”的梯次配置,使正规军的集中突击、地方武装的分散袭扰与民兵的游击消耗形成战术互补,创造了“正面有主力军、侧面有地方军、敌后有游击队”的全域打击格局,为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支撑。
“三结合”思想的实践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有效途径。“三结合”思想强调“主力引领—地方支撑—群众补充”的人民军队立体化建设发展路径,在保证抗日武装力量战斗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抗日战争中,我军主力部队能够迅速扩大,扩大起来的主力部队第一时间投入战场就具备很强的战斗力,依靠的就是党中央、毛泽东对“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进行的创新,和针对战争形势变化梯次升级、整体转化式的灵活运用。在民兵游击队中挑选具有一定作战经验和政治素养的骨干,组建成地方武装,这些地方武装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锻炼和整训,即可升级为主力兵团,而民兵游击队又可吸收人民群众中的优秀青年作为补充;在敌后抗战严重困难阶段,反其道而行之,八路军、新四军实行精兵简政,将大量干部送到地方武装、民兵和游击队中作为发展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的骨干力量。这种灵活的机制既符合武装力量建设的基本规律,需要正规军发展壮大时逐级升级,保证战斗力水平不降低;需要正规军精兵简政时逐级地方化,保证总体力量规模不减少,又能够最大程度激发各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逐级升级的指战员以升级为荣,情绪高涨、部队稳固;地方化的官兵,又能够有更大的空间发挥骨干作用,积极性也非常高。
毛泽东“三结合”思想在新时代的启示
理论的价值既在于指导实践,更在于培育思维。毛泽东“三结合”思想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彰显实效,更对当代战略博弈、战争指导及军队建设具有深远启迪。
“三结合”思想为大变局背景下大国博弈提供了新的思路。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美国固守冷战思维和霸权逻辑,对华遏制打压加剧。借鉴“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思想精髓,坚持国家核心战略力量与区域特色优势力量的深度耦合,既能以国家核心战略力量为区域发展指明方向、注入高端资源;又能以区域特色优势力量为核心战略提供配套支撑、拓展实践场景。这种“上下贯通、主次协同”的格局,通过高端资源下沉与区域实践反哺的双向赋能,打破资源分散化、力量碎片化困境,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业链韧性提升、战略资源保障等领域形成“1+1>2”的聚合效应,为应对大国博弈筑牢综合竞争优势。
“三结合”思想为现代战争开展体系对抗提供了有益借鉴。现代战争更多地体现在体系与体系之间的对抗,对抗形式的变化对国家武装力量内部系统、单元、平台、行动之间的一体化程度提出更高要求,进一步发扬“三结合”思想的内在优势,在当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含预备役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构成的武装力量体制框架内,遵循“需求牵引、能力互补”的原则,科学确定各力量在未来大规模联合作战中的职责任务、协同路径和转换机制,为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安全支撑。
“三结合”思想为实行新时代人民战争提供了广阔空间。习近平主席指出,不论形势如何发展,人民战争这个法宝永远不能丢,但要把握新的时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特点新要求,创新内容和方式方法,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信息化战争不可能简单复制传统游击战模式,“技术赋能、体系融合、全民智战”,将现代社会的科技潜力、信息资源、人力资源转化为人民战争能力是基本的趋势。借鉴“三结合”思想中军民结合、灵活机动的特点和精髓,通过转变思维观念,深度挖掘信息化乃至智能化条件下人民群众参战与支前方式,完善配套机制,实现新时代人民战争的战术战法创新;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实现动员效率的全方位、全维度跃升,使人民战争从传统“人海战术”升级为“技海战术”甚至是“智海战术”,才能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
“三结合”思想为提升军队现代化水平提供了基本经验。现代战争是精兵的对抗,借鉴“三结合”思想的基本经验,加强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途径就是军民融合。在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领域建设上克服小而全、大而全的两种极端,克服本位主义观念,跳出自我发展、自我保障的误区,推进军民融合战略走深走实。同时,将军民融合战略进一步向人才培养领域拓展延伸,借鉴军工领域军民融合的有益经验,发挥地方高水平院校的学科优势,逐步探索出一条军地深度融合、全域融合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新路,为人民军队现代化提升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灵魂,也是一支军队发展进步的灵魂。只有打破思维定式、更新理念观念,继承和发扬毛泽东“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思想在抗日战争中的创新精神和发展思维,才能在世界大变局中立于不败之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分别系空军航空大学航空基础学院教授,空军航空大学航空基础学院讲师)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编辑删除。)
|

